《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 | 阮昕:段义孚“天人合一”的心路历程

段义孚在书房
文︱阮 昕
“达人”者,义孚
段义孚何许人也?应该说,他在中国知识界,足可算一位“闻人”矣!记得不久前,一位著名建筑师在上海交大演讲时,对青年学子说他最喜欢的作者是段义孚,而且尤其爱读其《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我一时感动,当即自豪地告知这位建筑师,是我邀请并说服义孚于2005年到北京参加“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学术研讨会,算是《回家记》的促成者。义孚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踏上故土,感慨万千,返美后不久,文思泉涌,很快即成书《回家记》。

《回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回家记》英文版书影
在国内学界,我们通常将义孚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在西方学界,义孚著作等身,并收获诸多学术荣誉头衔,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达人”,却还称不上“闻人”。义孚曾经描述过美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如上过《时代周刊》封面和美国邮票的顶级“闻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对美国社会指点江山,俨然一副“家里大闺女”(daughter of the house)的派头。在和义孚多年的交往中,笔者时常私下臆测,以他的思想、才华和著作而言,假设也如米德一般对美国社会和公众文化产生巨大影响,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以义孚敦厚温雅的心态,或许本人的遐思流于世俗了。但若拿学问来提一提,义孚的学问人生似乎证明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主导下)的一个普遍现象:“达人”往往达不到“闻人”的影响度,而许多社会“闻人”,如一位睿智的比利时学者所言,他们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无任何智识(They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but understand nothing)。
物质载体
初识义孚,是从文化的物质载体入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风景园林学科开始关注义孚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1974)。从表面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如地质和地方,竟然与人的知觉、情感和价值观息息相联,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一道风景,如山林与海滩,经过义孚纵横古今却又举重若轻的梳理之后,印刻于不同文化和社会阶层的人心之中(有关“人心”将在后文详述),其含义及人对其的感情依赖,则经历了历史演化。于是,古时令人恐惧的黑山林竟变成了现代人怡养身心的度假胜地。如此这般,在义孚另一本名为《恐惧的风景》(Landscape of Fear,1979)的书中展现无遗。

《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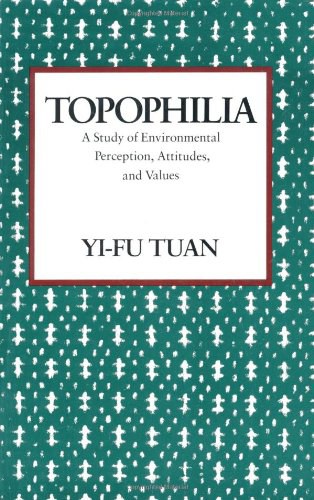
《恋地情结》英文版书影
或许是因为风景园林开了个头,义孚的书渐渐进入建筑师的视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加拿大建筑教授克莱伦斯·阿森(Clarence Aasen)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访问时即手捧一册《恋地情结》。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义孚的著作,当时也苦于一时无法理解书名。阿森教授后来成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导师,引导笔者从文化人类学入手研究人与建筑环境之间有意味的互动,则是后话。多年后读到义孚回忆《恋地情结》产生的“社会效应”,他十分得意地提到,一个著名棒球明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大学学地理,最喜爱的书即是《恋地情结》。这大概是义孚在西方世界接近“闻人”的高光时刻吧。
其实在八十年代的西方建筑学界,尽管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来考量民居,试图将人与人造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城市与建筑作为人类文化一个最有感染力和最为持久的纪念载体,仍是根深蒂固的主流。义孚虽从西学入手,将心理学——尤其是欧陆现象学中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和意识的“世界观”——用于人地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并发挥到极致。然而这种以知觉意识为导向、以人与物之间有意味的互动为目标的智识,在西方建筑领域从未成为显学。
以城市和建筑为例,西方文化对其永久性和纪念性的执着,古往今来,均在对“不朽”的求索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中古时期一个城镇的市民甚至可以几代人花费数个世纪的漫长时光去建造一座哥特教堂。义孚早年常坦言,中国传统建筑缺乏内向的空间性,于是在不同著述中,以哥特教堂的内部空间为例,生动描述透过玫瑰花窗倾泻到人间的天光,加上封闭的教堂空间里弥漫着来自管风琴的天籁之音、蜡烛的燃香、沙石砌块透出的阴冷潮气和触手可及的温暖木椅……如此多元渗透的感官“交响乐”,即是梅洛-庞蒂的知觉(perception)呈现矣!而知觉可上升到意识,于是哥特建筑这个文化载体,便将身体的感受转化为对天国的信仰了。
这不能不说是义孚对西方建筑一种优雅而又直观的集大成的理论总结,前提自然是物质的“永久性和纪念性”为文化精神的极佳载体。遗憾的是,西方近现代建筑偏离了这条主线,于是城市中的哥特教堂,从中古时期拥挤密集的城市板块中渐渐脱颖而出,到了十九世纪,往往成为华美宽敞街道的视觉焦点(vista);而哥特教堂本身也就变成旅游者从外观去欣赏的“视觉艺术”了。发展到今天便成了“网红打卡地”。
义孚对文化物质载体的关注点是超越知觉的,在《分离的世界与自我:群体生活与个体意识》(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1982)一书中,义孚以欧洲用餐的礼仪、剧场戏院的空间结构及住宅内部的房间组织,十分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从欧洲中古时期由松散交融的生活空间支撑下的“群体生活”,发展到十九世纪的分餐礼节、戏院私人包厢以及英国住宅中使用功能划分有序的一个个种类繁杂的私密房间,由此而承载欧洲现代文化中崇尚的“个人意识”。义孚自然是建筑界的局外人,似乎并未对现代主流建筑史家和建筑师在此背景下的一个奇怪现象发表任何见解:即他们更关注城市和建筑的视觉效应,而非空间组织对人知觉乃至意识的作用。笔者更为好奇的是,义孚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向性极为薄弱,那么他如何理解中国人的知觉和意识乃至“个人意识”呢?后文中,笔者将斗胆对此提出一个猜想。

《分离的世界与自我》英文版书影
人与物质载体
与其说义孚更关注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人知觉和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如说他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正是因为人的意识而带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其实才是义孚人文地理学的“地方”。
义孚文笔优雅委婉,虽以西学为主,却不见现代西方学者咄咄逼人的“批判性”(所谓criticality)。少见的例外,是义孚对“社会科学”的直言抨击——所批判的正是“社会科学”将研究物的方法用在人身上,完全找错了对象。多年前笔者和义孚有过一段电邮讨论,以各自学科(建筑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来对社会科学这个悖论口诛笔伐。
从人文地理的对象——人与地方(people and place)出发,义孚的大意经我发挥如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大学的地理学院,一群人(教师和学生)和一个地方(学院大楼),社会科学的方法首先从数据开始。我们收集方方面面的详尽数据,如教师们发表论文的篇数、期刊的级别、被引用率、基金的种类和当量、学生的来源、成绩、出勤、对老师上课的评教,再加上学院大楼的使用面积、教学研究各占多少……如此类推,难以穷尽。最终,通过某种计算,社会科学家可以对这个学院(人和地方)得出一个结论。往往以学科排名呈现,以量化的手段将这个地理学科描画为全世界第三名,因而区别于第二名。
我把义孚的命题讨论再略加拓展,在读了这一社会科学的分析和结论之后,我们如何知道院长和某位教授的私交如何?周五下午是否会一起去小酌一杯?我们怎么有可能知道某位学生每天走进学院大楼前的心情如何?义孚谈到文学倒是直通“人心”,让人体悟到一群人和一个地方的“内心生活”(interior life)。我们一同回味查尔斯·珀西·斯诺(C. P. Snow)的名著《学院院长》(The Masters,1950),此书将剑桥大学某学院里为了谋取下一任院长之职,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描述得淋漓尽致,即为“场所精神”(the spirit of a place)的佳例。通过文学艺术对一个地方的精气神的理解,是任何社会科学通过量化计算所无法企及的。
义孚还嫌对社会科学声讨不足,又写电邮补充:社会科学除了以数据为目标方法而造成的“扁平化”,还往往忽略了一个地方的最精彩和最拙劣之处,对“人的现象”(义孚英文原文为human phenomenon,笔者在前文已用了梁漱溟先生的“人心”,其实在此处更为妥帖,后文将展开)无能为力。以社会科学数字统计学的目标方法,个人竟无法超越在狩猎采集和初级农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我读后大呼精辟:我们又如何可以想象一部没有个人的人类历史呢?换言之,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个人。
我告诉义孚,他在现代建筑界里竟有一位志趣皆合的知音。美国二十世纪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 Kahn)曾断言:“莫扎特是否曾向社会请示他应该谱何曲子?自然没有!莫扎特谱写了乐章,而社会因为有了他而不同。建筑师则务必要创造能激励社会选择方向的作品。”
我向义孚表达疑惑,西方现代建筑师中虽有少数性情中人,将人对城市、建筑的多元感官体验浪漫化,如丹麦建筑史学家斯坦·埃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的《体验建筑》(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1957),把触觉、嗅觉和听觉与视觉同等对待,鼓励建筑师通过知觉的细微体验,感受一个环境、场地、房间的个性神韵。但总体而言,正如义孚常举的一个例子,现代世界如同一张完美的明信片。视觉世界的主导,令一个地方的精气神汇聚,换言之,给这个地方带来精气神的人退居次位,甚至近乎忽略。更谈不上通过对人居环境的知觉交响感受,进而上升到理念意识的层面了。
行文至此,似乎并不足以干脆地下结论,义孚的人文地理学即是心理学。义孚对城市建筑的稳定持久情有独钟。在与笔者的又一次电邮讨论中,义孚对当前技术至上的一个时髦建筑理论——所谓“环境回应建筑”,提出质疑。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筑空间可以依照人的意愿和对环境舒适度的需求而伸缩。义孚叹道,这简直是人的自信到了疯狂的地步!难道有那么一天,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理念会发展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而令窗外的一座山也随意膨胀收缩?外面世界亦会随由人的幻觉而融化?义孚于是再次重返西方永久纪念性建筑的初衷,那便是:生命即逝,人生莫测,稳定而永久的城市和建筑是生活所需的避风港!
我从未和义孚就此延伸讨论中国人的世界是否也需要这么一个稳定而永久的城市建筑“避风港”?通常而言,传统中国建筑,无论皇宫还是民宅,均为木构架,外部依附砖土墙体和瓦顶。相对于西方以砖石为主的宗教纪念建筑,持久性不是核心目的。2005年义孚游了故宫,曾叹其宽阔的庭院空间不足以给他哥特教堂所造成的感官刺激。然而义孚是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忠实粉丝,对其《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1957)中对建筑内外世界的二元哲思多有感同身受。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1977)一书中,义孚竟然用北京四合院来展示巴什拉所津津乐道的内外反差:“我们对内与外的概念可谓耳熟能详,但试想一下这些概念在此情景下会变得如此真实:一位客人在一场欢宴后离开灯笼照耀通明的院落,拾步跨出大门,踏入漆黑而狂风乱作的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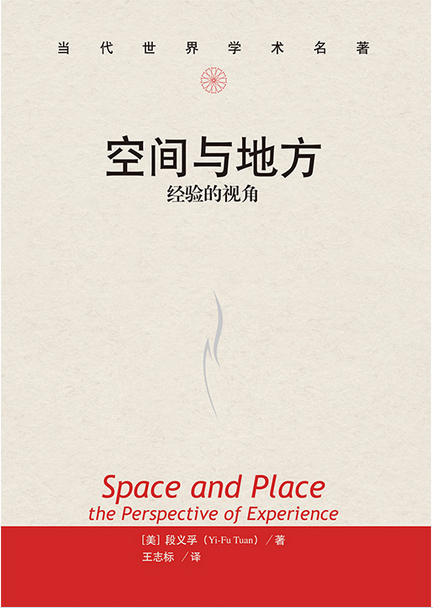
《空间与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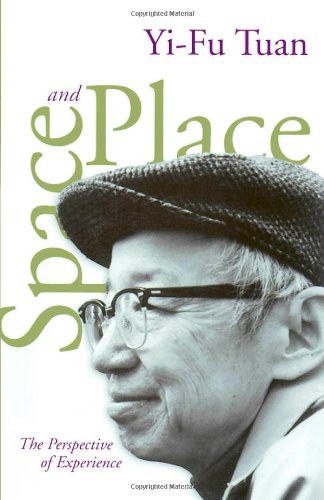
《空间与地方》英文版书影
义孚的一生从来未离开过学校,其漫长的育人治学生涯正式开始于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六十年代在这个小学校里,义孚和另外一位同事二人即组成了整个地理系。在1998年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演讲中,义孚发出幸运的感慨:由于没有多少发表论文和出书的压力,加上远离繁华中心的沙漠小镇,义孚得以自律和保持灵感,同时忘却了世俗的等级竞争,将思考学习的焦点集中到人文地理的核心点上,那便是文化与人性(culture and human nature)。等时光到了1969年,未及“不惑之年”的义孚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晋升到正教授时,他告诫自己,此生在世俗的功名就此足矣!义孚始终远离显山露水的东海岸名校,自1983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后,在此终其“求学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即是义孚1998年Charles Homer Haskins演讲的题目)。义孚虽多次暗中庆幸从未被要求出山担任系主任或学院院长等“为人民服务”的行政职务(倒是常受邀服务于奖学金委员会,做些愉快而施恩爱的社会服务工作),如此“修身”则是儒家人生,仅有闲官之职而得以拥有白居易理想的“中隐”了。义孚的“修身”有过一段十分独特的文学表现:数十余年间,他常发布系列“内部通讯”(newsletter),以书信的口吻寄给“亲爱的同仁”(Dear Colleague),其内容信手拈来,从学生的电话、电梯里同事间无味而礼貌的邂逅交谈,到“美学”的古希腊语词源……颇似士大夫营生处世之外的修辞成章、书画之作。

段义孚收到学生赠予的礼物
院落与“天人合一”
2021年,在笔者拙著Confucius’ Courtyard: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in China付梓前(直译是《孔子的院落》,但或许意译为《春秋·院落:中国人的建筑、哲学和理想生活》更贴切内容),去信义孚。虽然久未联系,我在信中将近年来从悉尼到上海的人生迁移给予几句淡描,主要是将书的内容向义孚做了简要汇报,书中还引用了义孚对胡同院落的怀恋文字。义孚立刻回音,开言道:“一个未经敬畏上帝来维系的道义世界!中国的士大夫们如何做到?这岂不是西方自由的世俗世界所梦寐以求!”(A moral universe unsustained by an awesome God!How did Chinese gentry manage to do that?Won't the liberal secular West love to know!)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此书期待已久[……]中华文明,其中心是院落,即一种以物质世界呈现中庸之道的建筑形制:它紧凑易得,合乎理性,遵循天道,顺应礼义。而现代社会在近几十年间将其彻底藐视,我们不禁试问,今后何去何从?不同于许多学术专著,阮昕[……]不仅参考了历史和哲学的传统史料,还讲述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迷人故事[……]
义孚一如既往地对拙著给予赞誉背书,我去信感谢,义孚回道:“我谈论你的书的文字并非慷慨之词 而是切实之语,或许孔子本人亦会如是说。”(My words about your book are not kind words, they are simply accurate words, a point Confucius himself might make)也就是在2021年10月,义孚和笔者共同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邀约做了“联合”采访。义孚是以笔谈形式回答提问,而笔者是现场答问的笔录,事先并无任何协调。访谈以联合形式发表后,题目虽是笔者即兴语出的“虚拟空间,在中国已存上千年”,笔者意识到义孚已真正回归中国传统院落。在向读者推荐笔者的拙著时,义孚提出“家常”(homeliness),那是绚丽的高层建筑图景所不能满足,一种唯有中国传统院落方可带来的安居感和亲密性。我猜想此时的义孚是真正的“回家”了(coming home to China)。这也应该是义孚最后一次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吧。
在这篇文字的行文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忖考量,如何对义孚的学问人生做一个总结。再读以上义孚为拙著背书的文字后,笔者恍悟:这段文字似乎描述的是义孚自己的著作,但更是义孚“天人合一”的心路历程。也正如义孚自己所言,他的学术著作其实是一部娓娓道来的自传。那么,义孚的人文地理学竟是通过自身对“人心”的一种艺术创作了。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
点击链接可跳转至:“上海书评”公众号阅读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JVqaSHCE0Lwm2Rs6Cksh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