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语境下的“传统”及其实践:
关于《建成环境中的传统:“真实”、超真和拟真》中译本的特别圆桌
圆桌嘉宾
奈扎•阿尔萨耶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
何培斌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教授
李晓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线上)
阮昕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
主持人
黄华青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梁宇舒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编者按:本文根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第18届国际传统人居环境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s,下文简称“IASTE”)双年会上举办的围绕《建成环境的传统:“真实”、超真和拟真》一书中译本的圆桌论坛纪要改编。论坛邀请原作者和多位深耕传统与遗产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对中文版的内涵及可能影响进行研讨。作为阿尔萨耶的代表作,该书涵盖了围绕“传统”概念的广阔议题,包括传统与乡土、传统与现代性、传统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与旅游,“真实”、超真和虚拟传统等,也是对IASTE这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组织30余年来的探索道路的全面总结,期待有关议题对当下中国语境下的遗产保护带来启发。
(原文刊载于《建筑遗产》2023年第3期第140-146页,有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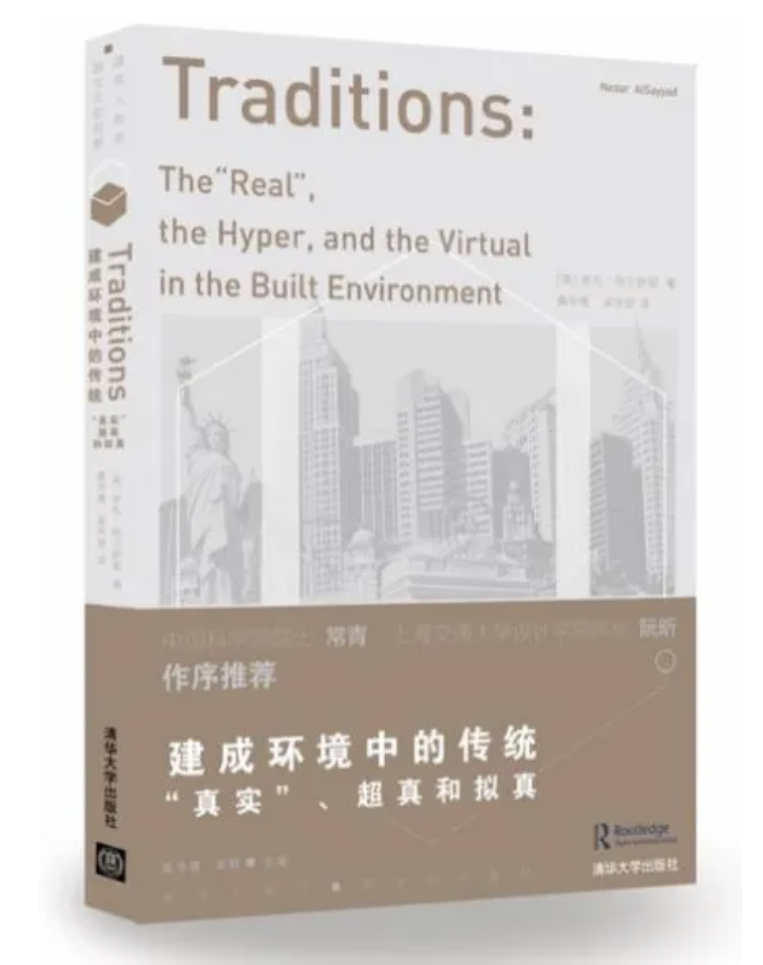
图1|[美]奈扎•阿尔萨耶 著. 黄华青,梁宇舒 译. 建成环境中的传统:
"真实"、超真和拟真[M].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06
引言:背景与议题
对《建成环境中的传统:“真实”、超真和拟真》一书中文版的讨论是从一个核心问题开始的,即当我们在中国谈论传统时,谈论的是什么?
在序言中,阿尔萨耶提出了关于“tradition”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困难。中文最广泛使用的翻译是“传统”,它本身就是个复杂的中文词。正如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国有多组二分概念描绘“传统”一词指向的场域。如经典的传统和民间的传统,指向官式建筑中的正统和中心性,以及民间建筑的多样和边缘性;历史的传统与现代的传统,指向传统的具体语境、演变过程及其动态性议题;传统的传承与传统的干预,指向历史环境中进行建筑干预的不同路径;还有真实的传统与虚拟的传统,指向传统体验的具身性与虚拟性的并置等。
中文版的两篇序言进一步延伸了本书的讨论。第一篇序言由建筑遗产学者常青院士撰写,他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霸权’支配和‘消费传统’浪潮的冲击下,与特定地域性及场所感相关联,作为身份认同及价值本源而得以代际相传的传统‘真实性’,正经历着消解、转化以至终结的过程。”这对于当下建筑学的发展境况而言是发人深省的,而从遗产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关注“传统在本质上何以是一种空间工程及其流程的核心命题”。“传统”的定位和定义在25年来的历届IASTE会议及阿尔萨耶引领的学术讨论中也发生着演变,如阮昕教授在第二篇序言中指出的:“一是传统从‘边缘’走向‘中心’,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于是传统聚落转向消费社会和全球化;二是传统以‘真实’渐变成超真和拟真。”本次会议讨论的即是这个“与时俱进、多变、复杂而具有创造性的新传统”。
由此,几位对谈人围绕主持人抛出的三个议题,多维度探讨了本书对“传统”概念的质询将如何在中文世界引发关于其历史基础、理论框架和实践影响。首先是“翻译”问题:如何在中文理论语境中翻译“传统”及其话语,考量其关键地位、深刻内涵和缠结情境,对其特殊性进行反思。其次是“割裂”问题:通过反思传统带来的割裂、挑战和机遇,重新思考“传统”在中国建成环境中的影响;诘问围绕“传统”的诸多关键概念,如现代性、风土、旅游、身份、民族国家等。最后是“重构”问题:讨论在空间实践中对于各种困境的解决方案,如遗产保护、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传统环境的虚拟化等。


图2-图3|第18届国际传统人居环境研究协会
双年会的特别圆桌论坛现场
1 观点
1.1
何培斌:
传统的概念化
我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IASTE自35年前开始的完整的学术历程,这正与我的职业生涯和学术关注点相吻合。我在读博时主要关注敦煌艺术史的课题,对其中的传统形式和空间非常感兴趣。到香港教书之后,我开始研究内地南方的乡村聚落和建筑,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对实体元素感兴趣,也对理解村庄或村民的结构,以及不同结构间的等级关系感兴趣,并持续关注他们的传统和仪式。
慢慢地,我从基于实体的研究转向概念性的研究,在考虑传统的概念性过程中,逐步与阿尔萨耶的思考路径契合,尤其是关于“超境遇”(hyper-condition)和“超传统”(hyper-tradition)等概念。我开始思索如何看待传统——不把它视为某种静止之物和会把我们束缚在某个时期的传统,而是一直在演变的传统,它不仅是某种建构之物。
我走访了内地很多村落进行调研,还请电视台去拍摄了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的碛口古镇。那几乎是个“垂死”的村落,基本没有人居住。我试图观察村落结构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与某些仪式的关系。非常巧合的是,在我第二次和电视摄制组访问那个村时,临县的戏班子来到村里的黑龙庙,在老戏台上表演,现场没有观众。戏班子是被一位信徒雇来还愿的,这是一场无需观众的表演,只有我们恰好在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传统?如何将这种传统概念化?在过去的十年里,附近这些“垂死”的村落经历过一个复兴的过程,试图发展旅游业,但大多失败了,因为它们不靠近主要的旅游资源。当地人试图复兴传统,却忘记了传统的社会文脉,忘记了生活在那里的地方社会,忘记了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活着的传统。之后,我们试图重新创造某种社会文脉,以便让传统可被理解为一种流动,一种穿越了时间、空间、不同的概念和许多不同的想象方式的流动。
在第17届IASTE会议上,我受邀做了一场关于《虚拟的传统》的主旨报告。我对这种文化保护形式很感兴趣,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保护什么传统,在呈现什么,又在代表什么?这种代表和呈现可能会形成那一刻的某种传统的快照,又是谁构建了这一传统?在研究敦煌石窟的数字化,或是绘画的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这些历史画作流传至今,其传统是否与我们有关?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什么,我们对传统的概念化经验是什么?这些不仅涉及表现的形式、呈现的性质,还涉及呈现的受众。这可能与阿尔萨耶关于“虚拟的传统”的想法非常相似。
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将一切事物呈现为一种美学观点。或许应有一种方式,让我们既能将传统理解为某个时间的快照,又能将它理解为不断变化的流动。变化才是恒定的;变化是我们应该定义之物,我们应用它来定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虚拟或数字的手段将是最便利、最适宜帮助我们呈现传统的流动性的方式。
1.2
李晓东:
传统与设计中的身份表达
我将基于我在设计中对于传统和身份的定义来谈传统,也谈谈历史和文化。我们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源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是西方第一个用鸟瞰视角来表现作品的建筑师。在西方哲学中存在主客之分,作为主体的人从正常水平视线来观察物体;而中国人则不区分主客体,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我们称之为“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图画都是以鸟瞰方式呈现的,其视角来自天。我们可见物外之物:建筑外的建筑,建筑外的山;我们看到了系统,看到了事物的层次。
还有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例子。中国的园林中能看到亭子、石头、水、树这些元素,但最重要的元素是廊。廊从来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拉长的、曲折的,因为我们需要动态地体验这座花园。日本园林中没有曲折的廊道,只有“枯山水”:你就坐在那里,观赏眼前的风景。背后的原因或许是,中国的风景是以黄山为代表的,远近高低各不同。要理解和认知整座山,你必须走近它,以动态的方式体验。而日本的风景是以富士山为代表的,无论从远处还是近处看,它都是一样的,并不需要走近去体验。建成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然景观的启发,这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我们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气候条件、材料等,以不同的方式建造世界。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人们开始以同样的方式造房子。建筑师试图用个人风格和个人身份进行反击,这确实丰富了建筑语言。但是,这就是未来吗?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联系,一种在建筑与现实、历史、文化和地方条件之间的对话;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建筑设计,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方式。
40年前,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我们试图向外部世界学习,但不知道如何做、做什么。贝聿铭给出了解决方案,香山饭店展示了他对中国当代建筑的理解,这是一座乡土的、可读的、风景如画的中国建筑。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建筑师一直遵循贝聿铭的方式。设计已成为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于是我们在中国各地都看到类似的建筑,它们都具有清晰可读的形式。
而我的解决方案是,试图适应当地的材料、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如何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因此,我最开始在农村做建筑。这是关于当代生活方式如何整合进入传统的世界观、空间观、序列观的设计;是关于当地材料的设计,关于传奇的故事如何转化为当代之物;这都是关于环境和当地社区如何能够被激励前进的批判性理解。
在我近期完成的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新校区项目中,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整合当代思想以解释这个特殊环境中的身份问题。这所高中的用地极为紧张,容积率约为5。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如何应对高密度、亚热带生活,以及学校的需求。这些问题怎么融合为一个整体?首先,跑道是在天上的,足球场也设在屋顶;我们设计了屋顶花园,一切都被划分为单元并嵌入到三维的场景中;我们在仅20000 ㎡的用地上设计了一个近3000 ㎡的花园,此外还有垂直绿化。创造力对教育机构是很重要的,打破边界非常关键。我们将可变性建筑元素引入到设计中,形成多样化的空间关系;也没有用实体墙将学校与城市分开,当你沿着街道行走,可以感受到这种诱人的空间魅力。
这一切皆关于空间,但并不关于实体。它是关于高密度的设计,是关于多孔性的,关于阳光的遮蔽,关于你如何在没有明确边界的情况下自由穿行,关于校园如何与整个城市融为一体。这是我对地方性身份的理解。
1.3
阮昕:
边缘与中心,西方与东方
我与那仲良教授(Ronald G. Knapp)共同主编的“Spatial Habitus: Making and Meaning in Asia's Architecture”(《空间习性:亚洲建筑的生成与意义》)系列丛书,其中包括不少关于传统的议题。我们一直默默观察着IASTE这个了不起的组织;在二十多年中,这套书出版了十多本,覆盖面很广,我们很早就邀请阿尔萨耶教授成为编委会成员。
翻译是件难事,我试图把这本书放在中国语境下。以传统的概念为例,英文中的“tradition”是否就是在中国所理解的“传统”?答案是不确定的。例如,当我们谈论书法,事实上谈论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calligraphy”在西方传统或印欧语系传统中是指“书笔的美化”,而中国的书法,大致可理解为一种“写作之法”。但中国“法”的概念与西方亦不同。在中国,写作的法则不仅仅是随性发挥,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关乎写作的方式。
关于IASTE,这个源于伯克利的大型学术组织的出发点,多少与这个地方的精神有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这种叛逆、先锋的立场而闻名,这种立场可能来自边缘性。作为来自少数群体的学者,掀起波澜,并试图使与学术主流不同的观点合法化,这很重要。曾几何时,他们是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和他的“东方主义”的追随者;但“东方主义”,如萨义德自己所宣称的,是一份职业或事业。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做这样的事情,即把一个边缘化的立场合法化,使它成为主流的一部分或与之平等的一部分。如果观察IASTE在过去数十年的主题,不难看到我所描述的这条轨迹。但不知何故,当“政治正确”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词被极右派和那些所谓的“左派”提出来,我认为自省可能会帮助我们反思这个理所当然的轨迹。
2000年在意大利举行的IASTE大会主题是关于“传统的终结?”(The End of Tradition?)它借用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本名著的标题。然而,福山下的结论有点早,新冠疫情基本上完全粉碎了他的假设。但“传统的终结”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这一被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即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是线性的;与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将历史视为一种线性发展。因此,福山的书在中国语境下可能会被认为是可笑的、过时的。
关于中国的传统,如果我必须为阿尔萨耶的学术发展历程补充一点背景的话,我认为是一场美妙的仪式:何培斌教授多次强调传统是一种流动之物,在中国,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中心位置;直至19世纪以前,它从未被边缘化。这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传统到底是什么?
中国还存在着一个长期的传统:述而不作,而非生产新的知识,这一观念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备受重视。孔子深知,发明新知识不是他的工作,重要的是对已经散失的优秀传统做出正确的阐释。孔子的一生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如辜鸿铭所言,孔子为中国传统的基本要素绘制了一份施工图。孔子知道,大厦已然倾颓;而这座大厦能否重建,是值得商榷的。在孔子之后,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是否是不变的、静止的,还是说,它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呢?
若套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著作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传统的发明》)的说辞,我们似乎已得出了某个结论:传统即是历史。但我又被优秀的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使用的一个比喻所震撼。他认为,描述中国传统的静态性质和动态性质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的最好方法,也许是看看中国绘画是如何表现瀑布的——从远处看时,它是静态的;但当你靠近时,它却是气象万千。
1.4
奈扎·阿尔萨耶:
IASTE的使命与“传统”的议题
作为对几位教授的评议的回应,我首先需要对IASTE的历史发展和理论语境做些回顾。“传统”这个概念在任何地方都是非常不同的,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根本区别。我撰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就是,这个词没有对应的说法。我一直在追寻传统的内涵,或围绕传统的实践,而不是在西方背景下出现的“tradition”这个词或其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决定了我们说什么。我喜欢阮昕教授关于书法的例子,它是对西方文化中业已存在的一个传统概念的极大挑战。
有时,当我们涉及某些类型的对象时,挑战一些现有惯例变得非常重要。无疑,20世纪80年代的伯克利是一个极具革命精神的地方。我于1986年开始在伯克利教书,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许多学生对乡土建筑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展示之处。1986年,我参加了乡土建筑论坛(Vernacular Architecture Forum),那是一个类似IASTE的团体;但我发现,那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美国小城镇,没有一场演讲涉及美国之外的论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IASTE诞生的原因。它的诞生不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关切,也是出于其他人的关切,他们都试图在学术界让这种讨论合法化。我们的第一次会议非常成功,有400人参加,那是在1988年,参会者有艺术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人类学家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建筑学家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还有保罗·奥利弗(Paul Oliver),他实际上是一位民俗学家。
确实,我的努力是将其中一些议题放到学术圈讨论的中心位置。阮昕教授使用的术语是完全正确的——“中心”和“边缘”;而我在伯克利的教育体制上所做的,就是把“边缘”带到“中心”地带,因为伯克利在当时绝对是学术界的中心。
我还想对“传统的终结”进行回应,它是在2000年举行的会议上产生的。这本相关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在它之前已有6本书在20世纪末出版,书的标题中都有“终结”一词。第一本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书,他是一位非常保守的作家,书名为The End of Ideology(《意识形态的终结》);然后是福山的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和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的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民族国家的终结》)。我决定按照同样的思路组织那场有针对性的会议。当时,所有人都在庆祝全球化。那个时候,互联网是新的自由空间,没有人能料到,20年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将收购推特(Twitter),大科技公司将控制公共话语。所以,我实际上是把“传统的终结”作为一个具体的话语来讨论的,但标题上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就是我说“传统的终结?”背后的意义。我仍相信这一点,特别是放在中国背景下。我从未主张也不相信传统可以终结,尽管有些传统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也可能会消失;我当时主张和相信的是,真实性不能再作为传统的首要定义条件,传统有很多其他方面可能会变得比真实性更重要。多年来,我对传统的定义受到IASTE的多届会议,以及我的许多同事的作品的启发。我把传统定义为一个“动态工程”,这个动态工程总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和特定的目的导向下,以当下为目标试图定义和重新定义过去。
我们应该记住,在“现代”概念被发明之前,没有任何人或社会称自己为“传统”;其中的二元论色彩是我认为有问题之处。阮昕教授引用了对我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传统的发明》,此外还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这两本书在我们的领域外奠定了学术基础,让我们得以理解传统的内涵,以此来处理由特定历史产生的传统。当我们仔细思索,会发现它实际上是被发明的,不一定有特定的起源。因此,有些围绕传统的实践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获得了独立于其起源的合法性。
我试图提出一个适用于物质文化所有方面的“传统”的定义,以便将其作为建筑研究的基础,例如珍妮特·阿布-卢戈德(Janet Abu-Lughod)在1990年IASTE会议上提出的“传统化”(traditioning)概念,即“让某个实践成为传统”的过程。我说“动态”,因为它永远不会是相同的。我对阮昕教授举的一些例子很着迷。您提出,在西方传统中,历史是渐进的、线性的;但在中国,您说它不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立于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讨论,将传统的概念操作化(operationalize),让我们所有人,不管来自何种文化,都能真正理解?
我想用一个存在于许多文化中的例子来结束这段讨论,它叫“家传的铁锹”。这把铁锹是由什么组成的?它有一个木制手柄,还有一个由石头制成的锹头;这两件东西原本是用草绳连接的。100年后,锹头损坏了,他们不得不用一个铁头来代替它;又过了一段时间,草绳磨损了,被钉子替代;最后,木柄本身也腐烂了,家人用一块橡木代替了它。构成这把铁锹的所有元素都不再是原有的,但那把铁锹仍被称为“家传铁锹”。即便所有的元素都改变了,它仍是家族的传统物件,得以代代传承。
在我看来,这个铁锹的“传统”有三个部分。其一是传递的理念,这是根本;其二是附着在这个特定物件上的文化意义,以及随之传递的想法;第三是随着时间推移而生发的价值,即它的“真实性”——这个部分,至少在我今天作为学者的立场上,不一定给予认可。我认可的事实是,这三个组成部分仍然存在,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已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使它们成为传统的原因。我并不是说这三个构成了这一特定的、有300年历史的物质文化的构件本身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恰恰是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过程。
2 对谈

图4|对谈环节
奈扎•阿尔萨耶
关于这本书,你们认为中国的读者究竟会关心什么?我也想请教阮昕教授,我构思这本书的思路和结构在您看来可能是西方的,但我想知道,我提出的这些主题,如现代性、乡土、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背景相关?如果有人要写一本关于传统的书,让它适用于另一个国家语境下的建筑环境,书的副标题又会是什么?
阮昕
关于这本书在中国是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它或许不会成为畅销书,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它在中国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因为“传统”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我在《序言》的最后写道,试图使一个类似“传统”这样的边缘化概念合法化,从西方的角度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是多余的,因为传统总是严肃之事。
至于您问题的第二部分,我是否试图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建立一种二分法。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把被边缘化或不那么被边缘化的传统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通常认为要小心类似东方/西方这样的刻板印象,但刻板印象中往往也藏着一些真理,它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意识的潜层结构里。我们不应轻视它,即使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现在让我们回到目前达成的共识。我们可以理解不断变化的,甚至非实体的环境,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意识,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此,或许反思一下中国关于“网络空间”的传统是有用的。如果有人说,中国人在2000年前甚至5000年前就有了“网络空间”,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因为西方的传统强调的是实体建筑世界,是可以触摸、可以凭靠之物;而在中国的传统中,这一点并不重要。在很久以前,中国人就明白,不朽的唯一希望不在于砖石,而在于文学。
让我举个例子。最近我写了一篇长文来纪念老友段义孚先生。段先生善于描述建筑空间及其对人们感知影响的方式。他对哥特教堂的描述是个经典的例子:如果说在13世纪,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同时走进一座哥特大教堂,都会受到巨大冲击,被感知体验所淹没,那燃烧蜡烛的气味、风琴的乐声、湿润的砂岩的冰冷触觉,以及木质长椅的温暖感……天堂般的光线经上方玫瑰窗的过滤倾洒而下;此刻,来自卑微阶层的人和来自贵族阶层的人立刻变得平等了……
这种从体验到认知的神奇转变会在很大程度上由实体环境促成。但在中国人的意识和理解中,当你描述一座月光下的美丽桥梁,或一座四合院时,房子的大小、形状、位置乃至场景的色调,都是不相关的。在我看来,文学的力量和“网络空间”或虚拟现实一样强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看到审美和传统的变化时,疑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或东亚文化和西方之间能否进行对话,或者这种二分法是否是虚假的,这已不是一般化的问题。我建议,我们应考虑特定的话题是否已经成为你关注的问题。如梁漱溟在讨论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这样总结:印度人太早意识到了问题,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死去;中国人想要延长他们的生命;西方的生命观念则是渐进式的。如果你未抵达这一点,印度人提出的问题对你而言就太早了……我们能否进行对话,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同的问题。
何培斌
我想再回应一下关于"传统的终结"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修辞性的。如果要讨论历史是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世界观,都有很多可以辩论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就像我们所概念化的那样运行。传统是否会终结?如果我们继续伴随它生活,或将它概念化、发明或重构,传统将永远不会终结。
我想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书名的翻译。本书英文标题使用了“traditions”的复数形式;但中文书名很难翻译复数。在某种意义上,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中国的传统,我们谈论的是这个5000年的传统,我们谈论的是单一的传统,而不是在更多地方发现的多重的、多元的传统。如果你以复数的方式来看待传统,显然你会不断继续下去,我们也将永远举办IASTE会议。
奈扎•阿尔萨耶
在许多其他语言中,传统总是复数的,它不以单数存在。你说传统在中文中不能是复数,这非常有趣。
梁宇舒
这本书伴随着我的博士生生涯,它成为我分析自己在内蒙古的田野调查的重要工具;我甚至用"传统"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标题,还在副标题中加入了"真实"和"超真"。但后来,我的导师给了我相反的意见,他担心这很危险。因此,我也想请教阮昕教授,您在西方和中国语境下都从事过教育和实践工作,您认为,当我们在中国谈论传统时,我们是将其放在怎样的语境中?又是在谈论什么?
黄华青
关于本书中文版指涉的“中国语境”,它既涵盖了中文世界的语言环境,更重要的是其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看待传统的观念。本书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是提出对传统采取多元和动态的看法。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重大进程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挑战性的。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传统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议程中被搁置一旁,但在最近几年,它回到了中心舞台。因此,我把阿尔萨耶教授的书带到中国语境下的出发点是,学术界和实践者应从过度符号化、单向度的传统,转向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共享、具身化的传统,一个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
阮昕
我认为,让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并无困难,即把传统理解为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因此,它可以被发明。即使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英国人如何发明他们的皇家典礼,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但我认为,仅有大的共识是不够的,关注到细微之处的差别或许更有帮助。这些细微差别体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让我们回到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传统,或许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传统,即“述而不作”。为什么孔子要坚持这一原则?据我猜测,这个传统非常悠久,中国的历史已成为一个宝藏和垃圾的大集合;但在宝藏之中,你仍有很多选择。与其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发明新的东西上,不如专注于这些宝藏,诠释它们的优良品质,使它们的生命得以延长。
我在序言的最后转述了南怀瑾的建议:孔孟之道为粮食店,每日必光顾;道家为药店,生病时要去造访;佛家为百货店,有钱和有闲时,可以去逛一逛。在中国,发明传统是否是件大事?可能不是,做选择似乎更重要。
何培斌
理解翻译的价值和阿尔萨耶教授提出的“传统”的价值都很重要。有价值的是,通过翻译揭示并讨论不同的力量,将它们提供给中国读者来思考并反观自身的潜能。要翻译“traditions”这个词非常困难,它提供了一个途径,以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传统,还有我们如何看待翻译。
奈扎•阿尔萨耶
最后我想说,我从不谈论历史,我不关心它是周期性的还是线性的;同时我又总在谈论历史,我出版的书很多是纯粹的城市史。最后,梁宇舒老师提到翻译本书副标题中的"真实"、超真和拟真概念时的挣扎,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翻译成阿拉伯语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没有找到对等词。也许我们将来应该召开一届关于"传统的转译"的大会。